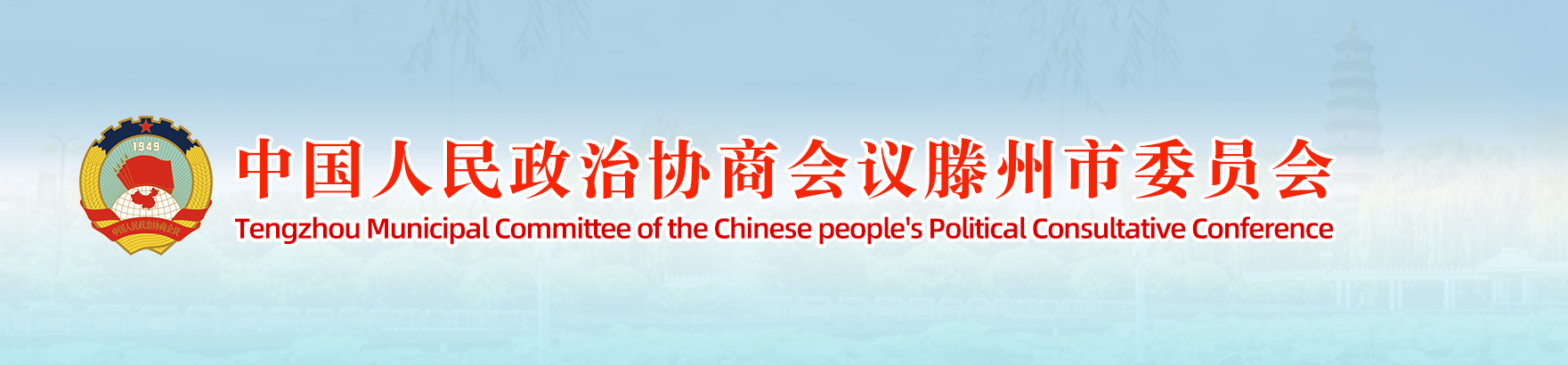
《复活》这部作品是列夫·托尔斯泰一生中最后一部长篇小说,笔耕十载,六易其稿,是其一生探索和思想的总结。小说通过玛丝洛娃的苦难遭遇和聂赫留朵夫的巨大转变,广泛而深刻地描绘了19世纪中后期俄国人民的生活图景。罗曼·罗兰说:“《复活》是托尔斯泰艺术上的一种遗嘱,这是最后的一峰,最高的一峰。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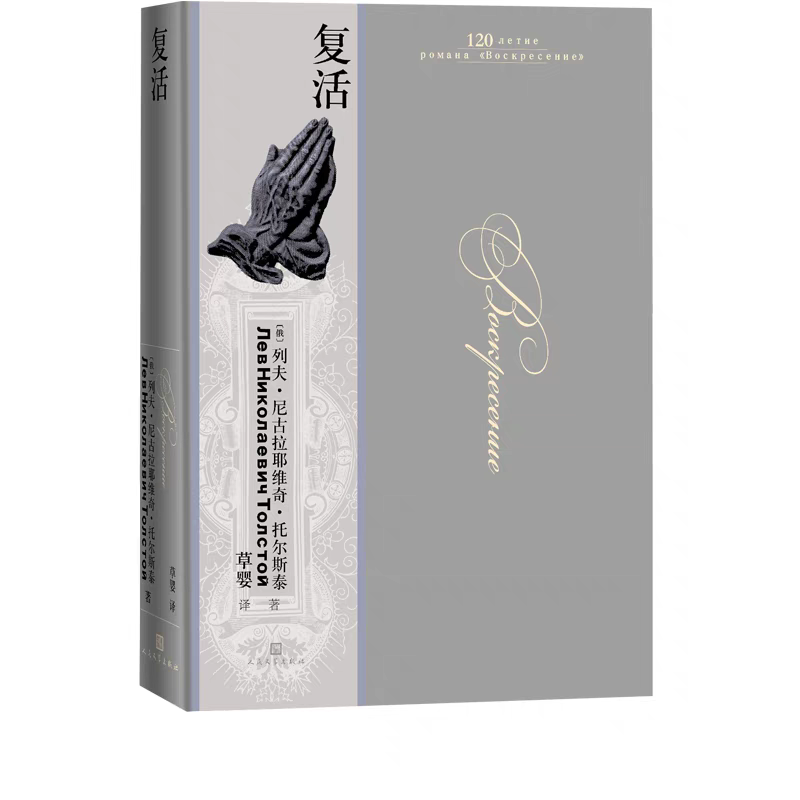
“复活”一词来源于《圣经》。小说力求反映男女主人公从“精神的人”堕落为“动物的人”,又从“动物的人”复归为“精神的人”的变换过程。
小说中女主人公玛丝洛娃原是个天真纯洁的少女,经男主人公聂赫留朵夫引诱而怀孕,之后便被赶出家门,从此染上恶习,沦为妓女。后来,玛丝洛娃因被指控谋财害命而遭到法庭的审判。这时,聂赫留朵夫以陪审员的身份出庭,见到从前被他引诱的女人,深受良心谴责。于是聂赫留朵夫开始为玛丝洛娃奔走伸冤,并请求同她结婚,以赎自己的罪过。上诉失败后,聂赫留朵夫陪她流放西伯利亚,聂赫留朵夫的诚意感动了玛丝洛娃,使这个女人重新爱上了他。在聂赫留朵夫的引导下,玛丝洛娃戒掉了烟酒恶习,也不再卖弄风情,而是选择到医院去做杂工。就当大家以为两人最终会在一起的时候,玛丝洛娃却选择了另嫁他人。其实,此时的玛丝洛娃早已不再是当初那个什么都不懂的少女了,她已学会真正地爱人,懂得为所爱之人着想。为了不影响聂赫留朵夫的名声清誉,她宁愿牺牲自己的个人感情与幸福。对此,聂赫留朵夫后来在日记里写道:“玛丝洛娃不接受我的牺牲,她要牺牲她自己……我觉得她的灵魂在起变化……她在复活了。”
聂赫留朵夫原本也是一个纯洁善良、追求理想的少年。他健康、真诚、充实、崇高,乐于为一切美好的事业而献身。他第一次遇见玛丝洛娃的时候,便被对方的美貌所吸引。只可惜,在踏上社会后,聂赫留朵夫变得猥琐、低下、空虚、渺小,他认为女人无非是一种“享乐工具”。于是,他诱骗了玛丝洛娃,这也是他放纵情欲,走向堕落的开始。后来,当聂赫留朵夫在法庭上,再一次看到那个被自己“断送了前程”的姑娘后,内心受到了极大震撼,从此踏上了自我审判与救赎之路:先由忏悔走向赎罪,再到甘愿为玛丝洛娃的幸福而牺牲自我,最终实现了自身的全面“复活”。
托尔斯泰在小说的最后写道:“从这天晚上起,对聂赫留朵夫来说,一种全新的生活开始了,这样说倒不是因为他已经进入一种新的生活环境,而是因为从这个时候起,他所遇到的一切事情,对他来说都取得了一种跟以前截然不同的意义。”此后,聂赫留朵夫不再是一个腐朽贵族,而是复活为一个不再追求浮华、懂得扛起责任的有志之人。这不禁让人想起《人间失格》里的一句话:仅仅一夜之隔,我的心竟判若两个人。
1869年9月,托尔斯泰在阿尔扎马斯的深夜经历了一场深刻的精神危机。这个被后世称为“阿尔扎马斯恐惧”的夜晚,作家在旅馆中突然被死亡的虚无感攫住,这种前所未有的精神震颤促使他重新审视生命意义。这场危机成为其创作轨迹的分水岭,50岁的托尔斯泰由此皈依基督教,形成了“通过信仰重建社会”的思想体系。这种转变在《复活》中具象化为对沙俄社会的全面批判:从法庭到监狱,从教会到土地制度,作家以手术刀般的笔触解剖着阶级社会的病灶,而主人公聂赫留朵夫的精神复活历程,正是托尔斯泰主义最生动的文学演绎。
面对地主阶级的道德溃败,托尔斯泰构建了包含道德革命、非暴力抵抗与普遍之爱的救世方案。“道德的自我完善”作为核心命题,强调通过持续的精神搏斗实现人性升华。在《复活》中,这种完善呈现为“精神人”与“兽性人”的永恒角力:聂赫留朵夫从沉迷情欲的贵族青年,到为农奴权益奔走的觉醒者;玛丝洛娃从被侮辱的妓女,到找回尊严的新女性,他们的蜕变印证着托尔斯泰对人性的辩证认知——善恶并存的生命体,唯有通过艰苦的自我净化方能抵达崇高。
托尔斯泰主义对“真正自我”的界定,突破了19世纪俄国知识分子的常规认知。作家将良知视为人性根基,在《复活》中创造性地展示了现代社会对良知的遮蔽机制:聂赫留朵夫初入社会时,发现遵循群体规范比坚持内心准则更易获得认同,这种异化现象恰是现代社会道德困境的缩影。当主人公开始质疑司法系统、土地制度和革命运动的本质时,实质是在叩问现代性进程中工具理性对人性的扭曲。托尔斯泰借由这些思考,揭示了制度化暴力如何将人异化为社会机器的零件。
在探索社会改良路径时,托尔斯泰坚决否定暴力革命。《复活》中革命者的形象被解构为三类:道德理想主义者、虚荣投机者与盲目追随者,这种分类暗含着作家对暴力手段的深刻怀疑。聂赫留朵夫在福音书中寻得的救世良方——无限宽恕,实质是将基督教伦理转化为社会改造策略。这种看似乌托邦的设想,在小说中具象为贵族与农奴的和解、加害者与受害者的互相救赎,构成对沙俄严酷现实的诗意反抗。
小说通过对司法系统的魔幻写实,揭露了法律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本质。托尔斯泰借聂赫留朵夫之眼,洞见了牢狱制度的荒谬性:它非但未能矫正罪恶,反而系统化地生产着新的罪恶。作家犀利指出,官僚体系中的个体在制度裹挟下,逐渐丧失了道德判断能力。这种制度批判延伸到经济领域,土地私有制被诊断为社会不平等的病根,而聂赫留朵夫分配土地的行为,则是托尔斯泰式改良主义的文学预演。
《复活》采用双重救赎的叙事框架,构建了独特的道德几何学。聂赫留朵夫通过“道德记账本”进行自我审判,其救赎之路经历了从补偿个人罪孽到承担群体责任的精神跃升;玛丝洛娃的觉醒则展现了底层民众的精神韧性,她在流放途中展现的人性光辉,颠覆了当时社会对“堕落女性”的刻板认知。两条救赎线索在福音书的照耀下交汇,形成“自上而下”与“自下而上”的双向净化过程。
这部文学丰碑的价值,在于它超越了具体历史语境的人性探索。托尔斯泰主义对道德自觉的强调,对制度异化的批判,对宽恕力量的信仰,构成抵御现代性危机的精神资源。当聂赫留朵夫在晨曦中翻开福音书时,我们看到的不仅是19世纪俄国贵族的觉醒,更是人类对抗精神虚无的永恒努力。《复活》最终昭示:真正的救赎不在于改造世界,而在于每个灵魂持续不断的自我革新,这种个体层面的精神革命,或许正是构建理想社会的隐秘基石。
荐书人:杨列敏,市政协委员,滕州市第一中学教师

